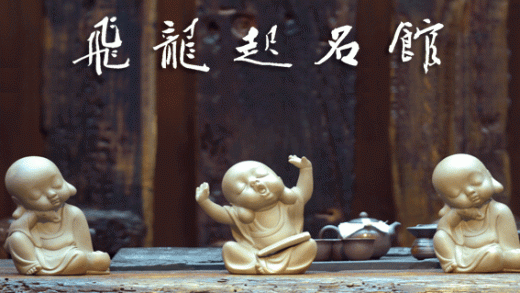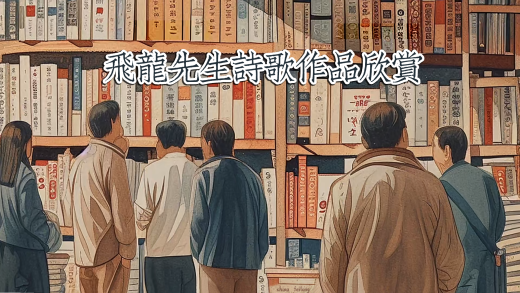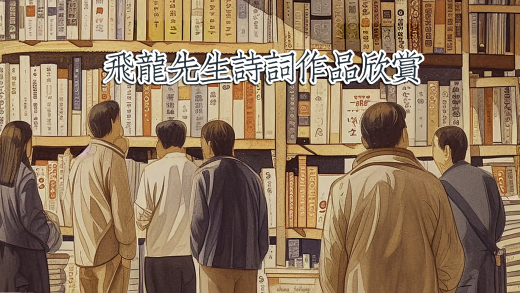文 / 王渊哲
(此文发表于《盐城晚报》2014年8月11日B24登瀛版)
骄阳正似火。饭碗一推,我来到屋后浓荫蔽日的林中,系上吊床,在悠闲的晃荡中小憩一番。阳光透过葱郁的树叶,呈现一片七彩斑斓的幻觉,仿佛春天还没走远,只有绵长的蝉鸣证明,这是夏日。
时光因之变的柔和而悠远,我的记忆固执地留在了这些蝉鸣中,它使想起儿时在乡下度过的那些夏日。父亲在堂屋东山墙的空地上,竖起四根木柱,再用厚厚的草帘搭成篷顶,名曰“小厂”。整个夏日的午后,我就是在小厂度过的,一张小竹床就是我的阵地:睡觉、看书、玩耍。时有阵阵凉风路过,好不惬意。
小厂旁长着水葡萄,葡萄藤机灵无比,顺势爬上了篷顶,给小厂增添了一丝绿意。几步之外的苍翠老榆,则有另一样的绿,与之相映成趣。这些都是可以舍弃的情趣,而聆听榆叶丛中的蝉鸣,才是我的最爱,它如同一段赞歌,如同一缕清流,引我在忘情的追忆中,一次次莫名的感动。
这只小小的精灵,曾带给我无数的快乐时光。我用一根细线栓住它的颈,然后一阵乱掌拍打,逼迫它飞行,它不得已飞了起来,发出“嘤嘤”之声,我旋转,它也跟着旋转,像个摩天轮。
听老人说,天牛触须上一段一段的斑纹,记载着它的年龄。于是我只要捉住它,必定先数一数触须有多少段斑纹,要是捉到大的,岁数比我还大呢。
黄天牛少,黑天牛多。黑的小而发亮,常常停在小厂的葡萄藤上、老榆树上。有时我也发发慈悲,玩累了,还把它放回原处。可它很笨,良久也不知逃走,仿佛我会善待它。也许此景独好,若是碰上我家的狸花猫,它就成了倒霉鬼,莫名其妙的做了猫的美餐。
收起吊床回家,抬头瞧见飞机掠过城市的边缘,好几秒停在高高的楼顶,像蜻蜓无声无息的飞过。
此刻,正是农村炊烟升起的时候,太阳倒在水稻田边,奄奄一息。我的眼前再现蜻蜓低回的画面:葡萄藤边、老榆树旁,它们时而飞来飞去,醉于夏日的黄昏,直至带走夕阳的余热;时而静立在葡萄枝头或是小厂的柱端,一动不动,似瑜伽的某个姿势,显得老练而从容,活脱脱的一幅水墨画。
有时我突然心血来潮,用自做的长杆小网兜捕捉它们,一路奔跑在村舍的小巷中,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,却乐此不倦。蜻蜓总能先知先觉的逃走,抛下我,独自在月牙初上的村口,无奈的叹息。
王渊哲写于梅花草堂
2014年8月2日下午

雨夜无眠
发表于2003年7月20日《盐城晚报》
夜已很深了,外面的雨越下越大,人们被连日来的梅雨缠得骨头发软,一躺下便进入梦乡。
怀有身孕的妻子早就睡着了,她那均匀的呼吸,使我感到雨夜的睡眠是多么的香甜!可我怎么也睡不着,被子湿漉漉的,像保鲜膜一样吸附在皮肤上;空气也湿漉漉的,弥散着一股淡淡的霉味,但并不难闻刺鼻,味道反而有点似丁香花。我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,眼光在黑暗中游离、游离……
不知什么时候,一声尖叫,划破这长长的雨夜,“不好了,大家快起床啊,房子进水了”。雨声想淹没叫喊的惊慌,但还是被我听到了,我立刻起床,脚还没着地,已进入水中。心里咯噔一下:糟了!雨水怎么就这么快溜了进来?房里太黑,我的鞋也不知被水冲到何处去了。打开灯,一看:呆了!屋里乱七八糟、一片狼藉。房门口漂浮着一个白色的大泡沫盒,里面是我新买的喷墨打印机,书橱已有三分之一下水了,许多书粘在一起,让人心疼。床罩湿了、地毯湿了,电脑纸湿了,地上的一切都浸泡在浑浊的水中。我呆呆地立在水里,看着眼前的一切,想叫想怒想笑,雨水的步伐声轻得如同蒲公英的飞行,无声无息地躺在我身边,我却浑然不知,真见鬼!我赶紧把还没浸水的东西移往高处,搬物的响声弄醒了妻子。她睁着朦胧的双眼,似醒非醒地问我:“深更半夜不睡觉,折腾什么?”再一看,不对啊!人在何处?床怎么在水中?我看着她恍如梦中的神态,忍不住大笑,她立刻明白了,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妻已没了睡意,于是我们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。等待天明,等待雨停,等待雨水退去。我再也不喜欢这雨夜,更不喜欢这无情的雨。在这个夜晚,它吞噬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财物,还有人们的心灵。在它的面前,我们的智慧显得多么渺小与懦弱。
今夜,我们无助、无奈、无眠。
王渊哲写与盐城洋西
2003.07.1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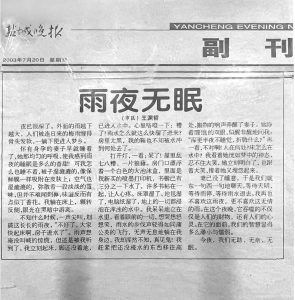
故乡清明
文/王渊哲
春夜多梦,朦胧中听得窗外沙沙雨声,辗转无眠。微明即起,撑伞步行至鱼市口,与兄弟同行回故乡,参加一年一度的祭祖典礼,风雨无阻。
青年路拉近了我与故乡的距离,城市与农村的界限,已让人无从分辩,只有雨中泥土的芬芳与麦子的清香提醒我,我们已行驶在城外的路上。我仿佛看到海子,他徘徊在田野与小溪之间,全身占满了野花的纠缠,他在思恋什么?是穷尽一生也未完成的夙愿,还是旧作无味新愁又添?听,他在风中絮絮叨叨: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……
我在农村也有一所房子,面朝小河,春天的河对面是一片油菜田,每到清明时节,花开似海,无边无际,而门前的那些桃花与梅花,也相继引春而放,一时争艳。远远望去,梅花桃花情深似海,不分家门,还有那门槛边无人问津的一丛樱桃树,也迎风而展,与之呼应成趣。
年年岁岁花儿相似,岁岁年年人却不同,与久违的故邻重逢,看着看着,他们就渐渐老去,沧桑的额头爬满枯藤,艰辛的微笑填满风霜,在简单的寒暄之中,我总是感到一阵隐痛,纵然满目绿茵依繁华,柳芽初出迎怀抱,我也快乐不起来。
人老了,故乡也老了,老宅因年久失修也变得老态龙钟。门前的砖缝中挤满了嫩绿的韭菜与雪荠,我小心翼翼绕行,生怕触痛它们。我轻轻推开孤寂的木门,仿佛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摔倒在地,墙角里锈迹斑斑的铁锹,感觉它已沉睡了好久好久,拂去木柄上的微尘,掖着它沿着潮湿的乡间小路,向父亲的坟茔走去。
我先要去看一看父亲,这是清明必温之课。雨凄凄,风潇潇,点点黄花映禾苗,我缓缓前行,努力寻找儿时欢乐的影子,也许脚下的泥土还存留着往昔我与父亲一起走过的足迹,或是一起散落的笑语,索索复索索,有凭却无凭,谁能作答,这顷刻的落寞。
或许经常眷念的一个地方,早已物是人非,空空荡荡的村口,是否还有一段灿然的花事等着我追忆,众多的浮云朝露在熟悉的阡陌中是否还有点点温存,与我困惑的一生因缘注定。
静静的走了一里地,穿过一片片的油菜花,全身都湿了。鞋子里的雨水与地面的泥水已沆瀣一气,潮湿的裤筒上冒着缕缕白气,头发上、脸颊上、衣服上都带着黄黄的菜花瓣,我感觉到丝丝冷意袭来。我站在父亲的坟前,一阵雨点湮没了我旷世的联想,幸福的过往不能复制,翻阅的光阴不会重来,我在嘘唏难过之间,感慨流年匆匆似水,一去不返。明天的风景可以重画吗?逝去的容颜可以重现吗?任凭千呼万唤,也只是恍惚的印象。
坟头多了软软的新土,它会向清明的细雨低诉,我曾来过。激动也好,感动也好,人生几何,对酒当歌。有缘也罢,无缘也罢,快乐几多,了无牵挂。人生难得几清明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春天的风景,她在最美的四月复苏,溢满清明的故乡。
注解:这篇散文本是发表于《盐城晚报》副刊的,由于错过了清明专版,故没有发表。此文写于2015年当清明。
2017年4月6日补记:2017年清明前夕,偶然翻阅此文,寄至报社,已刊出。谢谢主编,谢谢大家阅读!

|
|||
|
好多年过去了,时间慢慢淡忘了我的儿时印象,阿兰的影子成了一个记忆。蒙胧的记忆里,仍是住进城里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,家里的人已经全部进城了,但乡下的老房子却没有卖。 前几天,因乡下房子年久失修,必须找匠人修理,所以才回了趟老家。 我家屋后就是阿兰家,她家的房子比我家的还要破!她的父母因养鱼负债而背井离乡,一直没有回来过。阿兰跟她爷爷过,她初中毕业后去了大上海,不久爷爷去世了,接着,她唯一的叔叔也去世了,所以房子不住也没人修理了。不住人的房子更容易坏!不通风,不换气,鼠虫成群。 阿兰是我儿时的亲密伙伴。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存着儿时和她一起玩耍的片断:在一个初春的下午,我把她的一个泥娃娃抢回家,她哭着追到我家,我一急就把泥娃娃甩到门外,泥娃娃碎了,她哭了一个下午;又一次,在一个深冬的傍晚,我们去舍外放野火,我烧坏了她的新棉鞋,她去我家告了状,最后妈妈做了一双新鞋给她;再一次,她被人家欺负后找我打抱不平,我打伤了人家耳朵,还陪了人家医药费…… 往事真的太多了,历历在目,犹如昨日。我们常常在门前的竹林里一起学习,在门前的小河里一起游泳,在舍中的空地上一起过家家、捉迷藏,一起上学,一起放学,一年又一年,形影不离。人们常说我们笑话,看!多好的一对儿。 阿兰高中没能念上去,只有打工了,我去了小镇继续读书。别后一两年,还能听到她的消息,三年后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岁的养鸭子的山东人,也听说她父母因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与她恩断义绝。为这,我常常想象,阿兰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决绝是多么悲壮,而我一个大男人,却优柔寡断不如她。敢说敢当,言必行,行必果,也许我喜欢的就是阿兰的这个性格。她儿时的模样,可是她现在分明已不是当初清纯的阿兰。在我工作的第一年,听舍上的邻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,隔了两年,又听邻人说,她已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。我说不出什么滋味,小小年纪,跟着一个并不富裕东奔西闯的养殖户,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,该有多么辛苦…… 现在她什么样子,我想知道,但我无法知道,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有时对她的思念。也许相见不如怀念,怀念往往还有美好的旧梦温存,相见也许带来心酸的楚痛回忆。 门前屋后走几圈,泥土还是儿时的泥土,野花还是儿时的野花,却找不到儿时追逐的足迹,脚下松软的泥土沙沙作响,像是在嘲笑我痴情的回忆。
|